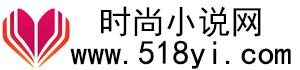第九十六章 老牛老去(2/3)
将衣服披在牛儿的头上,把眼睛给它严严实实地蒙住,让它看不见我的行踪。转一会我就遛岗了。歇息一阵后又去看看它,发现它拉磨如故,我便放心了。由于光着膀子,在这不卫生的大石磨环境中,牛儿随地拉大小便,污染了环境,便便滋生了蚊虫和小蠛蚊,时不时地叮咬我的身子,我便想逃离这个环境,回到阴凉的室内歇息。一觉睡去。父母从坡上收工回来,发现我还在睡大觉,便叫醒了我。我的美梦被惊扰,可也是大难临头之时。我哪里想到,那牛儿也不笨,趁我去遛岗太久了,自己也饿了,便甩掉了头上的衣服,大口大口地偷吃了磨盘里白花花的大半麦面粉,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在那个粮食极度缺乏的年代,几十斤面粉有多贵重,我作为十几岁的少年还没有体会到。这样一来,招来我被父母一顿毒打,特别是父亲找来一根木棍,打在我光身子上,痛得我难受极了。
我说:你们就是打死我,还能够把面粉从牛肚子里整出来吗?
父亲说我态度不好,不认错,又是几棍子,本来就过了中午,饥饿的身子哪里经得起硬木棍抽打。
我真的生气了:你这样打下去,难道比国民党还要残忍吗?你把我当地下整,还把自己当没当大人教育孩子?大不了就是几十斤灰面嘛,有什么了不起?难道我长大了,还挣不了几十斤灰面钱吗?
父亲再是惯性般的几棍子就软了下来,我此时产生了一种怀恨在心的念头,便导致父子感情趋于半个破裂。从此,再没有叫过他一声“爹”。这是全家,包括母亲是明白的事情。因为这次暴打,让我伤透了心,超过我想象,超过的承受力,这是我这一生中挨打最惨痛的一次,可谓铭心刻骨,痛彻心扉。我身子上的伤痛远没有心里的伤重。
我突然问母亲:牛儿死了一年了,怎么没有听你们说起过呢?
母亲想了一会儿说:你没有问起过,我们就不想说这个事,说了你会不高兴的。我们都知道,你陪护了牛儿十几年,有感情。其实,我们都舍不得老牛走,可有什么办法呢?
土地到户,各家自主劳动,队长改名为社长,其职责相对少了,担子减负,平时不再需要对生产劳动进行安排指导,大队改名为村委会,有什么精神就开会传达,加以认真落实。到了大小春归仓,稻谷小麦油菜进仓了,粮站的收购任务就按照各家各户土地的亩分分解下来。王社长不再需要每天敲我们院子后面田塝上吊在桐籽树上的老木塝通知上坡出工了,便选择了一个中午来到桐籽树下,把那木塝取下来,抱回了家收藏起来,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木梆不再使用,通知事情的时候,就是他站在保管室周围通知各个农家大院子的院长,比如我们大院子就是童家二哥,四合头就是马记工员,独山就是王老大,刘家塝就是刘会计,这样以来,队里的几大姓就算通知完了。我忘记说了,我父亲因为年龄偏大卸任了会计,人们一般称他为老会计。六爷也因为超龄了,主动辞去了副队长,这一职由独山王老二王怀接任。这样一来,王德海老队长已经做好了人事布局。姚家人担任的两个重要位置自愿交由老王的小舅子刘明当会计,同族兄弟王怀任常务副社长,保留了童家二哥的副社长,至于马记工员已经无事可做,不需要以前那集体生产时记工计酬了。正因为如此,我父母和六爷都是从国家工作岗位上下来的人,早已把形势看明白了,再占着位置也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于是商量后一起辞职,把位置让给那些个年轻人,也算是老干部**亮节,两袖清风。
其实在好几年前,我父亲和六爷都辞职几次,只因王队长再三挽留,没有变动。那是因为我家遭遇了原大哥被暴风雨和雷电击倒摔下悬崖痛苦而死的悲剧,六爷家因为大儿子鱼儿在龙王台河沟里的水潭里淹死了。这两件事情,让爱说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