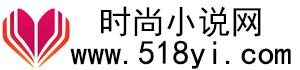40-50(11/27)
快,李辞盈两眼一黑,不由自主往前头趔趄了两步。自然的,有人不会袖手旁观,儿郎有力的手臂从旁边横过来,她就势攥住了他的袖口,稳稳站好了。或是天意,也或是巧合,李辞盈道完谢,松开萧应问手臂的那一刻,一张轻盈的赤色绸纱自他的袖笼无声飘落。
似有人于此时施放某种诅咒,风与辰光缓下了走速,李辞盈瞠目瞧着绸纱一寸寸落在地面,而那一声不可闻见的轻响好似当头棒喝,震得人脑瓜子嗡嗡乱响。
“这是什么?!”李辞盈很快把绸纱拾起来,也好似已拾到了所有答案,她不由自主地攥紧它,死死盯住面前波澜不惊的人,质问道,“萧凭意,这是什么?”
萧应问无从辩解,也从未想要辩解,挑眉长叹,答道,“这是那夜于砂海之中,某从昭昭腿上解下来的绸纱。”
李辞盈万想不到这人这样坦然,她气得胸膛剧烈起伏,又把绸纱向萧应问举近一寸,“郎君不要和我说,是陇西日光过甚,您迫不得已要将这破烂东西时时带在身边不可?”
萧应问摇摇头,说道,“三娘所谓‘破烂’,安知不能被他人视若珍宝。”
李辞盈懒得与他啰嗦这些,只颤声问,“你留着拿它做什么?!”
能做什么,萧应问干脆认了,“不错,就是昭昭想的那样。”他只怕气不死她,仍要补充一句,“浣洗的次数多了,才至于这般黯淡,不怪三娘一眼之下认不出它来。”
这下手中之物污秽到令人掩鼻,李辞盈脸色一变,拧眉将那绸纱直掷到了萧应问脸上,“恶心!堂堂十六卫总管竟这般厚颜无耻,您真就一点不觉羞愧?!”
立身十数年,从未有人敢这般不敬于他,萧应问冷笑一声,一下攥住了她的手,反问,“无耻?那日于城南客栈之中昭昭用尽全身解数,不就是想要某的这份‘无耻’么?怎么的,达到了目的就想逃,从不过问别人心里头作何感想?!”
李辞盈这点子把戏哄得住一时,可萧应问自十四就在台狱中陪审疑犯,仓促间的一点计谋,他要追究,总会找到蛛丝马迹。
萧应问盯着她渐渐发白的脸色,不留情面要她死得明白,“怪只怪昭昭太过聪明,非要将那信件做出笔法缭乱的匆忙样子,可惜了,笔法之着忙与用词之流畅格格不入,这样长的一封信,昭昭可是一个别字错句都没有呢。”
可那女郎今日不似往日那般认怂,李辞盈“哦”了声,冷笑道,“萧郎君不忿被小小女郎玩弄股掌之中,是以恼羞成怒,偷摸在背后使这种手段——”她惨然闭了闭眼,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可算是抽筋扒骨,让我永生永世也难再翻身了!”
萧应问眉头紧蹙,“你说什么?”
“敢做不敢认?!”李辞盈说道,“除了你之外,还有何人有动机将庄冲与我的关系告到兰州那边去?”
兰州来信,叔伯已找着了合适的李家子弟,再三道歉耽搁了郡守的事儿。
萧应问对这份突如其来的罪责十分诧异,“你能不能过过脑子想想,做下这事对某究竟有何好处?!”
李辞盈怒道,“让我不好过,你的‘目的’就达到了!”想着手儿还被他牵着,她挣扎两下未果,使劲儿往人家胸口锤了几下,“放开!!”
可萧应问非要说个明白,“问审判案讲究证据,你怎能仅凭猜测就将罪责强加于某?!”他冷笑声,“兰州之事夭折了,分明有许多可能,或是那位叔伯大限已至,等不及多在昭昭这儿耽搁,又或者裴听寒心意已变——”
李辞盈自前世回溯,怎会不知这两者不会有变,唯一的变数就在眼前,她不与他诡辩,立即扬声打断他,“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