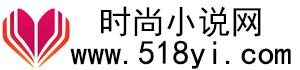40-50(17/27)
安,其他的她可没允准呢,点点头,“嗯。”此时一切虚无的诺言都不必多说,萧应问很明白她要的是什么,左右回长安也得月余,等事儿办成了再告诉她也不迟。他不由自主上前,俯身将脑袋搁在人家颈上,叹道,“收拾好行装,咱们明日启程。”
得寸进尺惯了,手掌就慢慢抚到人家脸上来,鼻息咻咻地靠近,又想吻她。李辞盈侧身躲过了,嫌弃地皱皱鼻子,“不可以,郎君方才吃过酱菜了!”
哦,酱菜,可真是扫兴呢,早知就不带了,萧应问一闭眼,只好退而求其次,脑袋倾到她颈后蹭了又蹭,“那昭昭欠某一回。”顿了顿,把日期也定好了,“明日补上。”
李辞盈才不答应,在他见不着的地方连翻了好几个白眼,又忍了一些会,那人只不住问了好几声,她不答应就不罢休似的,李辞盈到底没忍住捏拳在他宽阔的背脊上重重锤了两下,“晓得了,撒开!”
萧应问又中她一狠招,只觉着自个儿是肝胆俱裂了,咬了咬牙,“轻点儿。”
这大抵是李辞盈过得最难熬的一夜,一与姑母等说明了要往长安的事,一家人好似就是生离死别了——也不怪几人忧心,西京距此路途遥遥,她一去又是数月,教人如何放心得下。
李辞盈没法子,只得把萧应问的身份也与他们说了,本想是能令其安心,可惜在李家人心中,如此高位更不会将诸般蝼蚁当做人来看待,这一下哭声震天,好似她当即魂归了西天。
好说歹说是劝下了,清晨她又分别往陆家和青溪书塾送了绢布,唯念陆二娘与沈青溪能分神照顾家中一二。
辰时三刻,萧世子等人浩浩荡荡从肃州北门启程。都护府串谋案子牵扯颇深,光是疑犯就捉了一百余人,世子给鹧鸪山众倒还留了些脸面,令几人同挤在囚车之中。
而楚州牧一家十来口人并大几十个仆从,却都做五花大绑,串在一根捆仙索跟在兵将马后,以儆效尤。
当然,最让李辞盈不敢置信的还不在这儿。
昨日一夜未眠,她在车辇上颠了一会儿实在昏昏欲睡,左右她还顶着个李昭的名儿没人能管,就摘了帽儿,俯在小几上睡死过去。
再等醒来,李辞盈还当自己已不小心睡到了晚*间——为着早晨上车时此间宽敞明亮,这会儿周遭都暗下了几个度。
揉揉眼一抻腰杆,猛地看见个身影就靠在后边,惊得她半个哈欠又硬生生咽了回去。
“你……”李辞盈瞪了瞪眼睛,“你怎么在这儿?”
哦,尚是白日,只不过萧应问这般挺拔身姿遮在窗棂前,把光照都遮了个大概。
“某为何不能在这儿?”萧应问慢条斯理收了手中的卷册,张口就告诉她一个晴天霹雳,“昭昭上来时没注意前衡木上挂着的令牌?”
李辞盈那时昏聩无神,也没在意太多,跟着梁术就走到这辆车驾之前了,她瞪萧应问一眼,“就算这是您的车驾,您也不能如此明目张胆与女郎同乘!”
萧应问不理解,“某与李使君同乘,有何不妥?且某不过听从昭昭所言,伤好之前不便在他人面前现身罢了。”话语间顺便将沏好的茶水也递过去给她,“渴了么,喝茶。”
知法犯法无法无天!就再也不是见着裴听寒留在她帐中时那个咬牙切齿的老学究模样了——李辞盈猛地一愣,哦,原来萧应问那时是——
她撇撇嘴,真好笑!他有什么资格气恼?
李辞盈接了茶盏,就用毕生气力仰头牛饮而尽,再将它往小几上重重一拍,别过脸不想理他。
这人来此根本不做好事,只为纠缠她昨日在陆家院子里允准的亲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