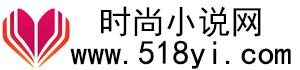110-120(19/27)
伸手要捂耳朵,那人得寸进尺地撑过来要拿她的腕子,鼻尖似蛛丝盘萦的晶润随着他的动作微微晃动,迤逦着、缓缓地落在轻勾的唇角,她不经意间瞧着了,实难禁羞赧。“怎不敢听?”萧应问笑了两声,捉了她的手儿压过脑袋,“胆儿这样小?”他覆身上去,眸中可有了做作的疑惑,“某可觉着满魏境也找不出第二个与昭昭一般胆儿堪比豺狼虎豹的女郎了,单是两句闲话就能吓着您?”
这是胆子的事儿么,此人乃混淆是非的一把好手,李辞盈瞪他,“闲话?谁人将这些当作闲话来说笑,妾瞧着是有人生了顶厚的一张脸皮,根本不知廉耻为何物。”
这就不知廉耻了?萧应问故作惆怅地叹一声,“冤枉,某可什么都还没做。”
话音落了,那女郎毫不客气的一脚就要踹过来,萧应问略挑眉,手掌下意识往侧边一撑,借力轻跃,躲开袭击安稳落地。
他震震袖口,幽灼的眸上染了笑意,“好险。”
涎脸饧眼,看着好不惹人讨厌,李辞盈恨恨道,“‘什么都没做’,你还想做什么?!青天白日,等会子有人过来,才教你我好看。”
萧应问笑,“飞翎在外头守着,怕也没人敢过来。”
至于裴启真,陇西出了这等子事,集议事忙,恐也顾不上别的。
道理都晓得的,可到底有人轻狂,李辞盈可懒得再辨,没好气哼了声,拧身一掀被盖了个严实。
萧应问不料她果真气恼,当即再不敢多说多惹,想了想,老实往盆架上拧了帕子,复又坐在榻旁好声哄道,“好了,是我不该这样,过来些,咱们先收拾了。”
让他得了“好处”,话语也显出蔼然来,李辞盈还有事儿请他办,慢吞吞又转过来,羞怯怯露了个毛茸茸的脑袋,任他揪了帕子给她擦拭。
一静下来,李辞盈可又觉得自个为之前几件事与他赌气十分可笑——他俩个岂能算得是郎情妾意么?闷起脑袋等人猜,做出这小儿女情态做什么,实则她最得意之事仍不过是他肯耐心为她做这些低贱活。
李辞盈思谋片刻,问他道,“是了,妾方才还怪了,陇西出这样的大事,吐蕃方又有异动,怎他几个往中厅议事,倒也没喊上您一齐?”
她嘟囔一声,“就算是如今眼疾未愈,脑子可仍然灵光呢。”
萧应问听罢,手上动作不停,“方才昭昭昏睡之际,某与官家等已做过商量,事儿差不多定下,也不必我再跟进了。”
李辞盈“哦”了声,不信似的,“不用您过去么?”
他照直擒稳了她的腿根,熟而生巧地一寸寸往下清理,“手里头还有别的案子要忙,后头咱们纳征、请期等许多事也需看顾着,恐有些时日不便离开长安城。”
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李辞盈总觉着有些不对,一说三叹的,“从前有裴家横在中间,官家尚且事事要您亲自处理才安心,没道理现下两家和乐了,倒少了您的差事去。”
萧应问笑,“怕什么,往后家里总归都交由昭昭来管,不愿日日见我,便把门儿拴着了,我住书房去就是了。”
李辞盈才不笑,吵过一次便罢,她不再翻这本旧账,“您手上的差事,可是大都督府遇毒一案?”想了想,又问,“苏校尉现下如何了?他究竟中了什么毒?”
提起此案,可就说来话长了,萧应问略一顿,点头,“苏君衡所中之毒,与庄冲所受应份属同宗。”
李辞盈猛地一睁眼,“大都督府上的人怎会有祆教密药?莫非是有人乔装潜入?这事儿果然与赋月阁的侍女有关?”
此时就将那事儿告诉她?萧应问摇头,“尚且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