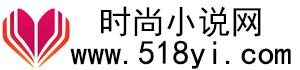100-110(37/41)
“当然了,要是喜欢的事刚好又很稳当,还是女孩子天然更擅长的,那肯定是好上加好。”她说完,轮不到其他人发话,陈定澜缓缓地问:“你才二十二岁?”
少薇“嗯”了一声。陈定澜往后却没再问什么,只是点了点头。
这桌上没有任何一个小辈敢如此大放厥词长篇大论指导人生,她平时闷不吭声的性子,一当出头鸟就当到了中央级领导的饭桌上,陈宁霄实在想笑。虽说都是家里人,但这种场面,如果他不收尾的话,桌上必会陷入冷场,让她感到压力和难堪。再说了,那位伯母的脸色已经是挂了又挂。
陈宁霄心里笑过,压平唇角,面对他大伯恰到好处的姿态——自家人,但带一份谦恭:“少薇比我更见多识广,尤其同情底层民众的遭遇和命运。前段时间碰上奥叔,奥叔原来早就是她粉丝,说她身上很具有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精神。”
少薇略低着头,看眼前德化白瓷盘周的浮雕,瞳孔微微扩大。奥叔什么时候说了?……
有他收尾,这话题算是击鼓传花给了他,场面必不会遇冷。
陈宁霄没告诉少薇的是,那天那顿饭结束,他和陈定澜在书房里有一场谈话。陈定澜问她是什么来历。
权力面前没有人有秘密,陈宁霄实话实说:“从小跟外婆生活,父母在她十岁时去外省务工,下落不明。”
陈定澜背手站在窗前,沉默许久,叹了声气:“身上不见逼仄,也很难得。”
人在向上相处时略有局促拘谨是人之常情,但性格逼不逼仄、酸不酸气,却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长期的压抑、冷落、不得志,一旦有了触媒,就会演变为攻击性,可能是振振有词力图自证,也可能是酸言酸语呛气冲天。这些随着经历刻进人的骨子里,纵使一朝得志,却也不是锦衣华服能掩盖,需要漫长的岁月去滋养——很可能滋养失败。
陈宁霄也默了会儿,眼前出现她最早在Root打工的形象。
“她有一颗包容心。这世上很多人,看任何人都只是在看自己,把自己的恐惧、欲望投射出去。她是看谁就是谁的人,真正的看见。”他看着他伯父的背影,“我想保护她身上这种神性。”
陈定澜身体一僵,其实不是不痛心。这姑娘好归好,但婚姻是另码事。
“你想保护,一定要保护到家里来?”陈定澜忍不住掏出根烟,一边点上,一边思索沉吟着,“她有才华,有心气,有格局,一点助力就能走很远。你想送她走到多远,我今天都承诺给你。这样不好?”
他问完,拉过自己亲弟弟生前坐过的那张办公椅,坐下,平静双眼自烟雾后注视着陈宁霄。
这一刻,他是他自己,又好像是陈定舟。是古往今来所有父权的化身,主持着年轻人的婚嫁,左右着他们的取舍。
陈宁霄不合时宜地想到了海洋馆里的那对俪虾标本。偕老同**绵里的硅质骨针,恰如牢不可摧的摩天大楼,给年轻的俪虾以庇佑,同时,也是囚禁。
陈定澜一直不紧不迫地盯着他,不放过他任何思考的细微变化。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错了,他的侄子没有在思考,而只是在冷讽。
年轻人的婚姻,历来是缴纳给家长的税费,或为换经济庇佑而自觉让渡出去的部份自由。
很可惜,他羽翼已丰,心意已决。
陈宁霄复又抬起眼,用与他大伯如出
一辙的冷静视线与之交锋碰撞,勾唇间落下散漫的两个字:“不好。”
偌大的书房落针可闻。
“我既要为她的腾飞远走助一臂之力,也要保护她这份悲悯心,这两件事,不懂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