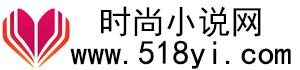40-50(17/27)
母的话刚出口, 便引来百官一片附和。“陛下不愿告知天下太子生身之人,也不愿将太子记入其他妃嫔名下,日后史书会说太子来路不明,便是为着太子, 陛下也当三思!”
“微臣不知太子生母昔年因何触怒陛下, 但望陛下念在其诞育太子, 于宗庙涉及有功的份上,宽恕一二,便是不入皇陵,也该有个位份,否则百姓议论起来,以为天子薄情, 又当如何?”
许是有人在其中推波助澜,朝堂之上一时间议论纷纷。
皇帝突然止住了朝中议论,朝太子问道:“此事我儿如何看待?”
太子上前,朝皇帝恭恭敬敬行礼,思忖再三说道:“儿臣觉得,父亲未曾追封生我那人,必有父亲的缘故。只是……儿臣自幼只见过父亲一人, 有时也想知道, 另一位血脉至亲到底是……”
“够了。”乐宿齐压着嗓音开口,与嗓音一道被压抑到极点的, 还有他的怒气, “我说过,我与那个人早已恩断义绝,你是我一个人的孩子,从未有过什么生身之人。”
沈彻闻猜测, 皇帝与太子父子二人似乎在那天就走上了岔路的两端。至此君臣父子,背道而驰。
紧接着便是落叶扑朔,凛冬悄至。皇帝接到密奏,说太子私下调兵,打算营救奉安公。
奉安公是前齐废帝,归降大燕后皇帝赐爵奉安公,将其奉养宫中。表面奉养,实则囚禁。自前齐灭国已有十八载,奉安公囚于知恩宫,一步未曾离开。
皇帝拿到密报后,立刻派人调查,竟查到了沈彻闻麾下有调兵痕迹,不由分说便以谋逆的名头将太子软禁东宫。沈彻闻也因此遭到圈禁,连辩白的机会都没能得到。
直到天授十七年初一当夜,太子万念俱灰逝于东宫。
沈彻闻从不觉得太子是病逝,坚持认为他是被杀的。毕竟当初太子并未被废,以皇帝对他的宠信,说不定还有东山再起的那天。沈彻闻猜测是有人怕他复起,迫不及待地杀了他。
沈彻闻后来曾在皇帝遗物中找到太子临终前的上疏,其上太子自称“微臣”,称皇帝为“陛下”,字句含泪,奏折末尾落有两滴氤氲的血痕。
“……为臣一世,克己复礼,谨遵储君之道,未料行差踏错,因贼子构陷与陛下离心,一己之身未能保全,以至今日,实有负皇恩教诲。微臣叩首,求陛下善待妻儿,勿责东宫之众……”沈彻闻断断续续,诵出记忆中的奏折。
太子脸上表情消失,眼尾似有泪珠滑落:“我想,或许我还有话未曾写完。若早知今日,不若当初留在抚朔关外,只做寻常父子。纵然天为被,地为席,风餐露宿,也好过如今琼楼玉殿埋枯骨,利刃寒芒刺血亲……
“彻闻,继续说吧。”
这件没头没尾的谋逆案,随着太子的仓促薨逝,在一片混沌中落下了帷幕。
或许是太子死前的奏折唤回了天家父子埋藏在争权夺利下的那点亲情,皇帝没有再对这件事进行任何后续追究,也禁止宫中谈论。只是沈彻闻依然被禁足。
直到年尾乐书音求情,皇帝貌似终于从丧子之痛的迁怒中走出,于隔年初春放出了被圈禁一年有余的沈彻闻。
自太子死后,皇帝身体也大不如前,病了几场,仓促地撒手人寰。他死前留下遗诏,要二皇子继位,善待太子遗孀。
乐书音登基后,封太子遗孤为顺王,与太子妃一道送入封地,太子一脉远离了京中是非。
至此,便是未来十年间,沈彻闻知道的所有与太子有关的事。
“我不明白。”太子听罢沈彻闻的话,脸上的茫然大过伤心,“我为什么要营救奉安公?父亲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