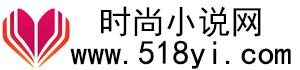30-40(7/27)
当自己是块香馍馍了,谁稀罕。”义愤填膺,豪气冲天,按李辞盈说,幼时阿姐就不该给他读那些志怪奇闻,她白庄冲一眼,“谁稀罕?我稀罕,若不是为着裴郡守前程光明、长安城又太过遥远的缘故,我倒十分不介意往傅六郎那边再使点子气力。”
傅氏盘踞长安,其背景冗繁复杂,实则这一句也算不得李辞盈的真心话,只不过她瞧不惯庄冲这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清高姿态——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真是金子打造的人儿肯为她如痴如狂,李辞盈怎么的也得从边角敲下些利好来,银子怎么赚也不嫌多,越是穷奢其华,握在手中也越觉着安宁。
怪就怪在这一句妄语之下,外头忽得就鸦默雀静,是一点儿声响都听不着了。
右眼皮止不住地跳,李辞盈心道自己不该如此倒霉的,下一刻风声震门,一只骨指分明的手握在了璀璨锦帘,随后轻轻一掀——
外间无数辉明顷刻聚于眸色,李辞盈侧开脸去避,余光辨清来者两人之面貌,真是悔得肠子阵阵抽痛。
此刻酣战已息,岐山营的将士们开始打扫战场,萧应问一柄寒剑当先,脸色之冷冽自不必多提,而他身后少年挺拔一张轮廓为炳彩日光描绘,神情也似焕上新生。
显然将她一句混话彻底信进去了。
自然是的,傅弦万想不到原来李三娘始终冷淡,只不过是嫌弃他无功名在身,比不得裴听寒能坐得肃州郡守的位置。
想攒些功名还不简单么?沉寂良久的心思如潮涌冲刷,傅弦情不自禁上前一步,想再求证李辞盈话语中有几分是真。
“三娘——”半句话没说出口,他只见得眼前一晃,辇上锦帘又重新落回原处,傅弦“欸”了声,皱眉看向萧应问,“我还有话没说完呢。”
话毕想绕开他进到车里去,可萧应问墙似的堵在那里,仍是半点不肯让开。
“说什么?”萧应问按住傅弦肩膀将人往后推了几步,扯了唇提醒道,“李三娘是什么人,你别忘了自个的身份。”
傅弦此时哪里听得进去这种话,断章取义重重点头,“她应当是还不知道我的身份!”
知道之后应该能拿正眼瞧瞧他的!
“……”萧应问匪夷所思,“我是这个意思?”
而傅弦思虑更多,见着萧应问敢将李、庄二人同搁在这马车之上,他倏然想起于砂海那夜,表哥特意提醒过要将庄冲留下,免他“日后追悔莫及”。
由此当知得,庄冲与李辞盈关系匪浅。
说破这事儿对李辞盈没好处,傅弦只冲萧应问感激一笑,想了想,突然问道,“表哥,上回你办咸州郡守妖言案,上边是如何断定的?”
那个案子证据确凿,萧应问也没多犹豫,漫不经意答道,“咸州郡守滥信祆教妖言,几番昏令致城郭百姓惶恐外逃,内阁以十恶论处,已判他秋后杖决了。”
傅弦笑了声,意有所指,“咸州偏远,郡守一职亦空悬,数月没找着合适的人指派,城里乱糟糟的,官家定是忧心得紧罢?”
话说到这个份上,萧应问如何不懂?他睨了傅弦一眼,“有人自幼立志高远,非历遍江河山川不肯归,如今不知怎么的竟甘愿安于荒野之地,你想想,若是县主知晓此事,你当如何?”
傅弦一摆手说“不会”,“我母亲怎会知道?某愿为官家分忧,自请戍边城,岂非‘志高远’乎?”他一停顿,看萧应问道,“当然,除非表哥说漏了嘴,没人知晓某是为了李三娘。”
“若要人不知,自己的尾巴先藏好。”萧应问往四周环顾一圈,轻哼一声,“见着李三娘眼珠儿都不会转,你能保证得了这里所有人皆能